优先权制度源自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巴黎公约”)。巴黎公约第四条规定,依照本联盟任何国家的本国立法,或依照本联盟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与正规的国家申请相当的任何申请,应被承认为产生优先权。巴黎公约还规定了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应该是该同一主题在联盟范围内的首次申请。
我国在1992年修改专利法时加入了本国优先权制度。现行《专利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设立本国优先权可以在优先权层面上使中国申请与外国申请处于同等地位,使得申请人在国内就相同主题再次提出的专利申请也可以要求其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因为本国优先权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所承担的风险来说并不突出,目前中国申请人在国内申请中采用本国优先权的情况不算多;另外,国内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核实优先权是否成立,在行政授权程序中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形不多。因此,目前要求核实本国优先权的情况在实务中并不常见。但是,在确权程序中,如果有涉及到无效证据公开日期位于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的情况,优先权能否成立作为突破点往往会带来很好的效果;而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对于要求有优先权的涉案专利其优先权的成立与否对现有技术抗辩至关重要,因此,优先权的核实在部分确权和侵权诉讼场景下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实际应用并不多见,但却是实务中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根据现行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4.6节中规定:审查员应当在初步审查部门审查的基础上核实:(1)作为要求优先权的基础的在先申请是否涉及与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相同的主题;(2)该在先申请是否是记载了同一主题的首次申请;(3)在后申请的申请日是否在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内。可见,在判断优先权是否成立时,除了要核实时间是否满足期限外,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是“首次申请”与“相同主题”,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不成立都会导致优先权不成立,进而可能出现在先申请成为现有技术被用于挑战在后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情况。
对于本国优先权中相同主题的认定,现行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4.1.2节中有明确定义,其认定标准在实务中包括有与新颖性标准类似或与修改超范围标准类似的方式,尽管因保护法益不同判断标准不会完全一致,但关于相同主题的认定标准,目前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上的分歧并不大。
而对于本国优先权中首次申请的认定,其相比于相同主题,业界关注和研究的并不多。现行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4.6.2节中对首次申请的认定给出了示例:一件申请A以申请人的另一件在先申请B为基础要求优先权,在对申请A进行检索时审查员找到了该申请人的又一件在申请A的申请日和优先权日之间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公告的专利文件C,文件C中已公开了申请A的主题,且文件C的申请日早于申请A的优先权日,即早于申请B的申请日,因此可以确定在先申请B并不是该申请人提出的记载了申请A的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因此申请A不能要求以在先申请B的申请日为优先权日。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和示例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对于实务中碰到的某些情形特别是对于本国优先权中首次申请的认定,行政程序中的认定标准与司法程序中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常常导致行政决定被司法判决推翻,这可以从人民法院的相关行政纠纷判例以及行政部门的复审或无效决定的观点差异中得以窥见。
在北京高院(2014)高行终字第1210号判决中,台湾地区的申请人(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先在台湾地区提出了申请TW200927787(优先权日为2007-12-27),接着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相同主题的申请200810007053.0(申请日为2008-01-25),之后又在中国提出了申请200910001233.2(申请日为2009-01-14,发明名称:可溶性聚噻吩衍生物及其于光电组件的应用),并要求享有在先申请200810007053.0的优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复审委)针对本专利申请作出的第48250号决定认为,TW200927787公开了本专利申请权利要求1-10的技术方案,且TW200927787的优先权日早于本专利申请的优先权日,可见在先申请不是记载了本专利申请权利要求1-10的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因此,本专利申请不能享有中国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复审委的主要观点认为,“推翻首次申请的证据并不一定必须是正规国家申请,只要能够证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申请的主题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就可以了”;并认为,“从优先权的立法本意看,优先权原则只是为了方便在不同的国家申请专利,尽可能以早的日期保护首次申请,因此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必须是某个主题的首次申请”。北京一中院作出的(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3069号行政判决,支持复审委的主张,维持第48250号复审决定有效。
但北京高院作出的(2014)高行终字第1210号的行政判决,撤销了一审行政判决和复审决定,要求重新做出复审决定。北京高院的主要观点认为:(1)优先权的立法本意,确实为保护首次申请,而不是首次做出技术方案,中国专利法以先申请为原则。专利复审委员会所提的“第一次做出来”,对于在后专利申请而言,可能构成现有技术,而不应成为阻碍在后专利申请的优先权成立。(2)相同主题的公开并不必然破坏他人申请的优先权。
2017年2月14日,复审委作出第119545号决定,撤销原驳回决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查部门继续进行审查,目前该专利申请经过继续审查后已经被授权。
针对该案例,笔者认为,复审委认为“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申请的主题尽管不是正式国家申请,但只要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不能作为首次申请“的观点尽管存在瑕疵,但从优先权立法本意来看,其实际上即已经是优先权意义上的首次申请,人民法院认为在大陆提交的第一次申请依然被认为是首次申请而能够作为优先权的基础,会导致优先权期限的变相延长,对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0年出台的58号规定,对台湾专利申请也给予了优先权承认,至此该漏洞算是堵上,司法与行政的分歧得以妥协。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底的一个案件判决可能会又一次放大两方的分歧,并必会会在业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和争议,该判决之后相应的行政处理及带来的后续效应也值得关注。
本案涉及的专利是专利号为ZL201110089122、发明名称为““电动独轮自行车“的发明专利,申请日为2011年4月1日,其曾要求在先中国申请的优先权(在先中国申请的申请日为2010年9月6日),上述两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均为陈和。与本案技术方案相关的是三件美国专利申请,均由ShaneChen(陈星)所申请,其中美国临时申请1的申请日为2010年3月9日,美国临时申请2的申请人为2010年3月18日,美国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为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行终910号判决中,针对本国优先权是否成立,推翻了第36591号无效审查决定(2018年专利复审无效十大案件)及一审判决。
在无效程序中,无效请求人提出的关键无效证据的公开日为2011年3月5日,恰好在本专利优先权日及本专利申请日之间,因此在无效案件审理过程中,本专利是否享有本国优先权,从而能否否定该证据的可使用性成为争议的焦点。
第36591号无效审查决定除了认定本国优先权规定中的“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中的第一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这一观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认为:对于具有相同技术来源的多份专利申请,即使申请人不同,也只有该多份专利申请中具有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可以作为优先权基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同复审与无效审理部的观点,维持了无效决定,认为对于具有相同技术来源的多份专利申请,即便形式上的申请人不同,也只有该多份专利申请中具有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可以作为优先权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12月8日做出的二审判决撤销了上述一审判决和无效决定,认为不应当仅以存在相同主题的申请为由,不审查申请人的主体是否为相同,就将首次申请作为享有优先权的基础。被诉决定以及一审判决关于“即使申请人不同,也只有该多份专利申请中具有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可以作为优先权基础”的认定,于法无据。即最高院认为,本案申请人为该相同主题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专利申请,该申请人应享有优先权这一权利,其应当可以作为在后申请的优先权基础。
本案中复审委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相同主题的专利申请已经出现过,不是该相同主题的首次申请,所以中国的首次申请不满足优先权中首次申请的定义。但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因为在先申请与中国首次申请的申请人不同,对于中国申请的申请人来说是首次申请,因此享有优先权。
笔者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观点持保留意见。本案中两份美国临时申请和本专利具有相同的技术来源,专利权人原本可以主张美国优先权,但是专利权人放弃了法律赋予的权利,重新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并试图作为首次申请以主张国内优先权,这种要求中国优先权的行为已违背了巴黎公约优先权的本意,实际上变相延长了优先权的期限,导致同一技术方案保护期限被变相延长。如果对此不作限制,专利权人就可以利用不同申请人无限制的提出优先权请求,势必导致优先权被滥用,影响公众的利益。
目前,该专利无效程序还处于合议组审查的法律状态下,相信专利局无效审理部对此依然还在研究讨论中。目前来看,无论是从前一个案例中专利局实审部门、复审委与北京高院关于同一主题的技术方案是否是首次申请的认定存在的分歧,还是后一个案例中复审委与最高院对优先权中首次申请的认定标准大相径庭,复审委的认定标准基本是一致和连贯的,但与北京高院或最高院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即行政程序中更关注相同技术主题及第一次申请的认定,而人民法院更注重优先权的权利这一法律属性本身,两方都试图从优先权立法本意上对各自观点进行解释,这也反映了两方在优先权立法本意以及国内优先权的立法本意的认识差别。作为专利代理师,我们希望最高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能够就此观点给出相应的说明或更明确的操作指引,便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优先权制度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摘要
在判断优先权是否成立时,除了要核实时间是否满足期限外,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是“首次申请”与“相同主题”,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不成立都会导致优先权不成立,进而可能出现在先申请成为现有技术被用于挑战在后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情况。因为本国优先权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所承担的风险来说并不突出,目前中国申请人在国内申请中采用本国优先权的情况不算多;另外,国内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核实优先权是否成立,在行政授权程序中需要核实优先权的情形不多。因此,目前需要核实本国优先权的情况在实务中并不常见。但是,在确权程序和专利侵权纠纷程序中,对于要求有优先权的涉案专利其优先权的成立与否对现有技术的认定及现有技术抗辩至关重要,因此,优先权的核实在部分确权和侵权诉讼场景下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目前来看,专利局实审部门及复审委对优先权中首次申请的认定标准基本是一致的,但与北京高院或最高院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行政程序中更关注相同技术主题及第一次申请的认定,而人民法院更注重优先权的权利这一法律属性本身,两方都试图从优先权立法本意上对各自观点进行解释,这也反映了两方在优先权立法本意以及国内优先权的立法本意的认识差别。作为专利代理师,我们希望最高院与专利局能够就此观点给出相应的说明或更明确的操作指引,便于我们更好地应用优先权制度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撰稿 | 李佑宏 张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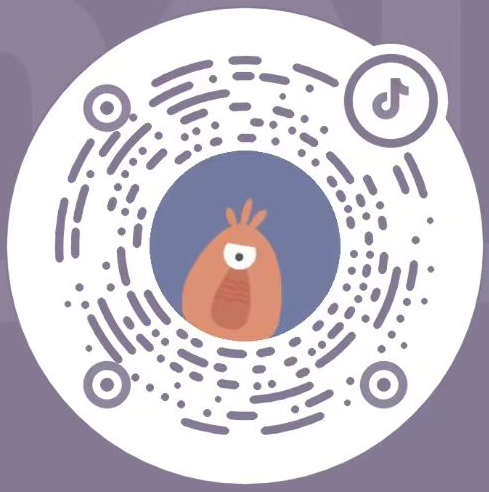 关注抖音
关注抖音 关注微博
关注微博 关注微信
关注微信 鄂公网安备42018502007324
CopyRight @ 2013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鄂ICP备18021336号-1
All Rights Reserved
鄂公网安备42018502007324
CopyRight @ 2013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鄂ICP备18021336号-1
All Rights Reserved


